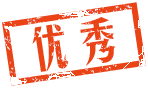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扎根树 于 2013-11-12 21:06 编辑
我 的 老 师
翻过险峻的二瞪眼山,就进入一座古镇,长途汽车在一个很小的车站前停下,停车吃饭的时间很充裕。古镇上的民居青瓦石墙,楼台错落,紫蔓掩壁;条石巷道,或短或长,或熙攘或僻静,幽远古朴。10里主街尽头,高耸的三瞪眼山崖腰上,一条弯曲的青石古道,在慢慢升腾的雾气中时隐时现,崖下万丈深渊诡秘莫测。女人坝下洗衣,木桶担水。男人萧笛斗笠,牧牛竹林。这里很像一幅田园画作,人们悠然自得,没有些许哈尔滨市防空战备的紧张气氛。坐下来,一张木桌一家人品尝着老家江西的赣南菜肴,一条瘸腿大黑狗在桌下窜来窜去。吃过午饭,几簇翠竹后面,忽然传来一阵朗朗的读书声:“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循声望去,一个敞开窗子的教室里,一位女老师正领着小学生们朗读课文。从12月12日因疏散办理转学离开学校,到现在已经十几天了,眼前的情景,又让我想起了我的老师。 我的小学女老师张勤民老师,是四川人,戴眼镜,二十五岁左右,文静秀气,课讲得很好,很严厉有责任心,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非常受同学尊敬。 上一年级的时候,张老师站在讲台上,用教鞭点着黑板上新学的拼音、生字一字一顿地教我们的情景,清晰得像一张张照片印在脑海里: 波 坡 么 佛, 得 特 讷 勒 ( b p m f d t n l); 日 月 水 火, 山 石 田 土。 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飞成个人字,一会儿飞成个一字。 张老师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教导,点燃了孩子们心灵的智慧之火。在张老师的引领下,顽童们告别昨日的蒙昧,踏上了寻求知识的道路。 上二年级的时候,一次张老师让同学到黑板前写生字,我和很多同学都踊跃举手,不一会儿,黑板前面已经有好几个同学在写生字。老师叫我写“谁”字,这个字当时认为很难的,我在黑板上写好,回到座位上坐下,心里美滋滋的,实际上我并没有写对,只写了半个“谁”字。张老师笑呵呵地走到我身旁,和蔼地告诉我说还缺言字旁啊,再去加上吧。我把言字旁加上又把单人旁擦去了,老师说还是不对,然后手把手教我写完“谁”字,我的人生中“谁”字是这样学会的。从此以后,我记住了“谁”字,也改掉了粗心的毛病。 六一节前的一天下午,张老师到教室通知门丽针、张林和我三名同学,第二天上午到学校集合,去儿童公园参加迎接外宾活动,要求穿白衬衫蓝裤子扎红领巾。当时红小兵组织已经取代少先队组织,大家都没有红领巾,需要去借红领巾。不知什么原因,张林骂了同学,被同学告诉老师了,张老师很生气,狠狠批评了张林,取消了他参加迎宾的活动。 张老师由于身体不好,几天都不能来上课了,同学们都很想她。一个男老师来代课,教乘法口诀表,他不认真教课,敷衍了事,还贬损我们:“10个和尚里有没有混1个秃子,谁知道呢!”张老师终于来上课了,同学们可高兴啦。她提问我们乘法口诀,大家都不会。张老师问同学们背诵口诀表没有,同学们说代课老师没告诉背,大家也不知道需要背诵。张老师立刻布置大家回家后,每天必须背诵一列。经过几天的提问和课后背诵,大家就都会乘法口诀了。
冬季下午3点多天就要黑了,轮到我们班上街宣传。张老师把1岁多的孩子托付给同事,执意要领我们去,怕我们不安全。到了西大桥我们每人站在一根电线杆子底下,一字排开。大街上过来一个人,我们就大声背诵语录。天黑了,大街上行人很少,从我面前先过来一辆卡车,我大声喊:“要斗私批修!”一会儿过来一个骑自行车中年人,他骑到那里,我们同学都高声背诵语录,到我跟前时,我昂头挺胸严肃地背诵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那人还冲我笑笑,我心里很高兴,觉得我也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电灯杆上的灯亮了,把路都照亮了,我们的街头宣传就要结束了。张老师把同学们召集起来,一起过马路,然后,张老师嘱咐大家要及时回家,不要在路上贪玩。她站在寒风里看着我们远去,我们走的很远了,她还在不停地向我们摆手,可她的小宝宝还在学校里。
69年上三年级的时候,中苏关系紧张,城市里的玻璃窗都上贴米字条,随处可见人们在挖防空洞。我们学校——哈尔滨市贵新小学也在挖防空洞,高年级学生要下去挖地洞,低年级运土。
我们学校的防空洞很小不足以容纳所有学生,防空警报响起时,我们几个年级要到校外一个大防空洞里。
张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在洞外用脸盆把土运到校门口。我没拿好铁锹把脚不小心碰了一下,但我仍端土走在前面,我的伤口被张老师看到了,她关切地问我,是不是被同学弄的,我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的。她担心我的脚伤,不让我端土了,但我愿意和同学们一起劳动,我们端着盆象小燕子似地飞快地跑着。
张老师经常家访,了解每个同学的思想动态,关心每个同学的学习和家庭情况,对待学生就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呵护。她常恋恋不舍地说要送我们到高中毕业,我们也非常喜欢张老师。为了响应国家疏散的号召,我家就要回江西老家了,再见了张老师,再见了学习三年的学校,我会时时想起这段难忘的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