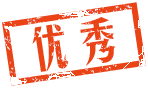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陆华 于 2014-5-4 18:32 编辑
莫言旧居行
去冬路过高密市,专程去了趟东北乡,参观了莫言的旧居,碰见了他二哥。所见所闻,所感所悟颇多,使我不得不写下来。 一 参观高密市一中的莫言展馆后,我赶到东北乡莫言旧居,那时日头西落。负责接待的莫言二哥管谟欣(下称:管二哥)已经劳累一天了,依然不辞辛苦接待了我们。感动! 小小的院子里挤满了人,参观的、购书的、买纪念品的和等着接待的。时间这么晚了小院还这么热闹,是我没想到的。而且后面还陆续有小汽车的鸣笛声,和院外走来的男女老少的欢笑声。 随行的陈圣是当地年轻作家,给我介绍:自打莫言获奖后,这个小院子,这个小村落,这条通往高密的公路,这个连接四方八面的高密市就人流如注。春节大年初一,这里也是络绎不绝,源源不断。到了九月份高粱红的时候,这里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多的时候五六百人,少的时候也得两三百人,有来自香港的、台湾的、还有英国的、法国的,院子里都站满了人。说到这里,小陈脸上现出欣喜,骄傲。这是东北乡的骄傲,是高密人的骄傲。随着莫言热上升,这种状况预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旧居大院门旁写着“莫言旧居”表明这个建筑物的属性,四周没有其它衬托。一排红瓦黄墙的土房,便是莫言曾经居住过的旧居。旧居的泥墙上嵌着一块刻有“莫言旧居”的大理石。五间老屋的破损处现出用新泥修葺的痕迹,最西头房间里还摆着农具。莫言青年时期用过的碗、书橱、箱包等存放在最东边的房间里。厢房里,摆在炕上的小桌沾满了灰尘,靠墙的柜子上还摆着一台老式收音机和几张大红的“福”字。莫言获奖了几年了,小院没有扩建,仍旧是土墙、农舍,残旧的屋瓦、狭长的村路,空旷的高粱地,以及泥土弥漫的芬芳。 院子里常年有管二哥来接待来宾。后来实在忙不过来,就把他妻子、女儿叫来帮忙。屋内一人,给参观的客人讲解介绍。院里的人,负责售卖莫言的书籍和纪念品等。 我走进莫言旧居,和管二哥握手致意。刚刚给客人讲完莫言的故事,他嘴干舌燥,顾不上喝口水阴阴嗓子,又继续。我和他是同龄人,他所说的莫言的经历我既能听懂,又能理解,还能和他交流沟通。可能基于这点,管二哥对我更亲热一些。管谟欣说:“我现在每天都得来旧居开门,村里邻居说我都成为“专职导游”了。有时来晚了,就会有游客打听着找到我家去。我不管自己手头有什么事,都会尽快过来为他们讲解。他认为,客人们从不同的地方来此地一趟不容易,不能慢待人家。 在离开院落时候,管二哥赠送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其实我并不是最远)两本书,我当然不能无功受禄。他还为我签字署名并且合影留作纪念。其他客人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走出院子时候,黑色天幕就要慢慢落下,还有人闯进院里。迎面碰上来人,顺便问了句:“从哪里来的?”“济南的。”“河北省的。”“河南的。”人们操着地方口音回答。 莫言从这里走向了世界,这里又吸引着全国、全世界各地的客人。这里见证了一代文学大家的成长。莫言的旧居是那么的吸引人!人们争相参观的热情和踊跃购书的场景,深深印在我的脑际。 二 在高密,在东北乡,提起莫言除了那些文学爱好者,政府官员熟悉,老百姓们也知道,但都非常含蓄,不张扬。这是因为莫言一家的言行低调。低调到什么程度呢?莫言获奖的当晚,他正在家里。评选结果公布后仅在高密市的一个饭店里通报一下,市有关领导简单庆贺。莫言从自家五楼下来到四楼大哥家,接受了几位客人祝贺后,又回返自己家里。尽管莫言住处附近有鞭炮声响,也没有过多宣扬。在乡里,人们平静地接受喜讯,没有大轰大嗡。旧居依然宁静,生活还是那样平常。就像没有这回事儿一样。管二哥说:“莫言获奖后一直提醒我和大哥要低调点,老百姓出身,没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游客从很远的地方专程赶来参观莫言旧居,这是对莫言的最大认可,也是对莫言莫大的鼓励。莫言不在家,咱不能摆架子啊。每天我至少要和游客合影上百张了。”管谟欣表示,“原来这院内鲜有人来,自从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游客太多了,这大门在白天时间就没有锁过。” 莫言家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上个世纪初,高密东北乡还蛮荒一片。平安庄是一个只有几十栋土墙草顶的房屋,村庄虽小,村中央却有一条宽阔的黄沙大道,道路两旁杂乱无章地生长着一到深秋便满树金叶、不知其名的树。黄沙大道一直向东延伸,蜿蜒出村外,连接了一片草甸子。春天,这里绿草如毡,星星点点、五颜六色的小花朵,宛如这毡上美丽的图案。草甸子里有叫声婉转的鸟,有快如闪电的野兔,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在蓬勃地生长。这些动物和植物,日后都成了莫言的朋友。对于不幸出生于那个时代的莫言来说,记忆中最深刻的压抑,就是饥饿与孤独。 管二哥说,这座宅子,莫言生活了整整二十年。最近十多年,这座宅子就一直空着,无人居住。老宅是1911年建成的,1966年进行了翻新。这里承载着莫言太多的记忆。他在这里出生、长大、结婚、生育。1987年拍《红高粱》的时候,母亲还住在这老宅里,家里人都将这座宅子视为一种美好的回忆。莫言从小就喜欢看书,但我们这里是农村,农户家能有多少书?在二哥的记忆中,小时候的莫言活泼好动,非常爱读书,把附近村子的书都看完后,开始翻新华字典,一本字典都被他翻破了。他小学五年级辍学后开始割草、放牛、给棉花喷药、割麦子、推车,劳动之余,莫言跟着大爷爷学了两三年中医,看过《本草纲目》。管谟欣也学过中医,但是他认为弟弟学得更快,掌握得更深。 在管谟欣眼中,三弟不是什么大作家,就是一个庄稼户人、平常人。他的文学道路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 管谟欣说,莫言在文学方面是比较有才华的,做人比较低调,很执着。大哥管谟贤是莫言在文学上的启蒙者。莫言小时候的书包里,时常装着大哥中学时用过的课本和写过的作文。 莫言到部队后,开始和大哥通信。莫言告诉大哥,他想走写作这条路,一开始,大哥是不同意的,他最担心的倒不是弟弟只是小学五年级知识水平,底子薄,而是因为当时搞创作容易被“上纲上线”。可是他不走这条路干什么呢?莫言的单位全是技术干部,他只是个当兵的,站岗。站岗能干什么呢?站两年岗就回农村了,于是就同意了。这些信,大哥一直保留着,工作调动时,搬家十次,这些信都没丢掉。 后来莫言模仿孙犁的文章写得很好,选择支持弟弟的大哥告诫弟弟,从事文学道路,一定要坚持、能吃苦,一定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走自己的道路,这样才能在文坛上立得住脚。当时,莫言写好作品后就会邮寄给大哥请他修改。 管谟欣比莫言大5岁,今年62,高中毕业后,就在村里做农活,之后做过农业机械,如今已退休在家中,照看已有93岁高龄的老父亲。哥哥与弟弟都出门在外,家里总的有人照顾,孝敬老人,服侍双亲自然落在管二哥肩上。如果说莫言的文字从来没有离开过高密东北乡,二哥管谟欣则是从没离开过这块土地。对于到高密市或者到北京的生活,管谟欣并没有多少兴趣。他牵挂着家。 管谟欣毕业后的工作也与文字紧密相关,做过乡里的通讯报道员,在《潍坊日报》上发表过通讯报道。后来又做了乡里的司法所长,退休前在乡上的县志办公室工作。 管谟欣是高中毕业生,在那个年代也算是村里的秀才了。那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因为弟弟莫言的获奖,在村里种地的管谟欣格外忙碌。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当晚,凌晨一点多,已经睡下的管谟欣被瑞典电视台电话叫醒,要求采访莫言,后来他吃了三片安眠药才睡着。
诺奖公布后的一段时间,在莫言旧居,阳光穿过木格窗棂,照进土屋土炕,这个存留着他们哥仨童年记忆的地方,他接待了很多来自国内外前来参观的记者和游客,
管谟欣的印象中,小时候的莫言是个“调皮蛋子”,他好动,也贪玩,什么都喜欢摸摸看看。回忆起莫言小时候的样子,管谟业的脸上也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时候与莫言“抢书看”的经历。管谟欣说,当时因为村里人读书的不多,家里的条件也不富裕,能读的书就只有家里留下的古书和小人书。所以每次只要家里一有新书,莫言就和二哥管谟欣开抢。“因为,每次莫言看完书就喜欢把书藏起来,当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别人都看不到了。那时候,晚上看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看书,母亲常常提醒莫言,没油了,别看了。但往往被莫言当做耳旁风。”莫言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嗜书如命的程度。为了换取别人的书看,莫言就去给别人家推磨,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着书回来,他都是满脸春风。 在管谟欣的记忆中,莫言上学的时候语文成绩很好,而且还有一个特殊嗜好,就是背《新华字典》。正着背完,倒着背,有时候,问起哪个字在第几页,莫言都能答出来。管谟欣也常常因为弟弟的这些聪慧而觉得自豪。莫言今天能够得到认可,也是他自己一步步努力的结果,他吃过的苦在几个兄弟里是最多的,农家的孩子一步步走出来不容易。回忆起莫言当兵前在县城打工的日子,站在莫言旧居里的管谟欣突然语调低了下来。莫言18岁的时候,父亲让他到县城的胶莱河去干活。当时他不想在最好的年纪丢掉书本成为一个靠劳力吃饭的人,但是因为家庭条件困难,兄弟姐妹多,已没有钱来供他念书。 由于莫言身子还没有长壮实,刚到工地时,只能拉锁链,两双手的掌心常常是被勒出一道道血痕,破了长好,长好了又被勒破。因此,直到现在,无论谁提起莫言有多大的成就,说起莫言的作品多么富有感染力,管谟欣都笑而不和,他心里清楚这些为人瞩目的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孤独和心酸,“大家看莫言的作品,看到的是大悲大喜的情节和故事,而我看到的是他的童年、他的成长和不易”。 虽自莫言当兵后,兄弟俩基本分居两地,但管谟欣对莫言的关心却从未因距离的拉远而减少过。莫言每次有了新作他都会关注,但“莫言的各类小说和散文出得太快了,有时我们也来不及看”。 近几年来,莫言因创作和公务繁忙,回家的时间也少了,时常是年节里回家看望年迈的父亲和渐老的兄长。“父亲和我都希望莫言能在外健健康康的,至于得不得奖、排不排名都无需放在心上,安心做好自己喜欢的事就好。莫言这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希望他能够不骄傲,继续以此为新的起点,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路。” 莫言回忆童年时说过:“我的二哥(管谟欣)也是个书迷,他比我大五岁,借书的路子比我要广得多,常能借到我借不到的书……他看书时,我就像被磁铁吸引的铁屑一样,悄悄地溜到他身后,先是远远地看,脖子伸得长长,像一只喝水的鹅,看着看着就不由自主地靠了前。他知道我溜到了他身后,就故意将书页翻得飞快,我一目十行地阅读才能勉强跟上趟。他很快会烦,合上书,一掌把我推到一边去。但只要他打开书页,很快我就会凑上去。”好一幅兄弟打闹的童趣图! 三 莫言的本名叫管谟业,因为以前话太多,言多必失,索性笔名叫“莫言”。提醒自己别因话伤人,省下来的精力,都释放在小说里。沉默之后的莫言变得喜欢思考,这种思考成全了他的创作。 莫言强调,自己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写作。他不是居高临下的,他是身在其中的。 小时候在家乡上学时,莫言的文学功底很好,作文写得非常漂亮,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诵。1967年小学五年级时,他因文革和得罪别人被迫辍学回家务农,当起放牛娃。莫言曾说,他小时候之所以想当一个作家,就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就是想娶石匠女儿当老婆。 莫言这样描述自己的诞生:1955年初春,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17日,农历乙未,正月二十五,属羊。这是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平安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庭成分为富裕中农。 莫言不像村里其他的伙伴,失学后就把学校里的知识全都忘了。莫言很爱学习,他把家里有字的东西全都读遍了,过年时,房里墙上会贴上报纸,莫言读完书后,开始读报。如果报纸是竖着贴的,莫言就歪着脖子读。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他们精神的根据地。没有精神根据地,盲目地胸怀世界,表达的可能就只会是一些蜻蜓点水一样零碎而浮泛的公共感叹。他必须有一个用一生来持续地辨析和陈述自己的地方。这个地方要能真正容纳他的智慧、情感和心灵,能让他激动,让他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和智慧去书写。高密东北乡对于莫言,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莫言用自己坚实的作品,把故乡高密东北乡,带进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和殿堂。作为一个骨子里浸透了农民精神和道德的作家,乡村文化、齐鲁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因子在莫言的血液中有着深厚的积淀。他的理想精神,深深地扎根于高密东北乡这块土地,这块“血地”由此也成为见证他不断成功的文学根据地。 提起莫言,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电影《红高粱》里那些色彩鲜艳的画面和黄土地上张扬的生命力,那就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高密不仅仅是莫言地理意义上的家乡,更是他几十年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一直苦心构筑的文学故乡。他的小说创作几乎从未离开高密,那是独属于他的文学王国。他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开叙事,并向历史纵深挖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延伸。 1981年的一天,在军营的莫言收到一封保定市《莲池》编辑部的信,他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同年,他的女儿管笑笑出生。 《莲池》是河北省保定地区文联主办的内部的文学期刊,是现在的《荷花淀》的前身。莫言的小说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即发表于此刊一九八一年第五期上。当时,莫言深受孙犁先生的影响,小说是诗化的散文化的。在此之前,他曾给包括《莲池》在内的很多地市级的文学期刊投过稿,但从未发表过。《春夜雨霏霏》在《莲池》上发表,是莫言文学生涯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里程碑。 1983年,莫言《莲池》上,又发表了一个题为《民间音乐》的短篇小说。在读过莫言的《民间音乐》之后,孙犁曾经问过当时在孙犁领导下担任编辑工作的老作家:“你知道青年作者莫言吗?”回答说不知道。孙犁说:“你看看,我觉得写得不错,我要介绍他!”于是孙犁在《读小说札记》第一节中,推荐与称道了莫言的这篇小说。孙犁写他对这篇小说的总体印象是:““去年的一期《莲池》,登了莫言的一篇小说,题为《民间音乐》。我读过后,觉得写得不错。”孙犁说,莫言此作所写,“事情虽不很典型,但也反映当前农村集镇的一些生活风貌,以及从事商业的人们的一些心理变化”。还说,这篇小说的写法“有些欧化,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对莫言的小说《民间音乐》作了中肯的评价。 莫言说,当他在文学上蹒跚学步时,孙犁先生为他所写的评论,让他终生难忘。莫言知道,能够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那篇评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而,对于孙犁先生,莫言除了敬佩,还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在孙犁先生逝世之后,莫言说:“中国只有一个孙犁。他既是位大儒,又是一位大隐。按照孙犁的革命资历,他如果稍能入世一点,早就是个大文官了;不,他后半生偏偏远离官场,恪守文人的清高与清贫。这是文坛上的一声绝响,让我们后来人高山仰止。”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莫言对孙犁先生的极其尊崇。 莫言在接受河北媒体采访时也曾说到:“我的文学是在河北起步,我的命运也因河北而改变。” 1984年秋天,尚不知名的莫言得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著名作家徐怀中先生的赏识,进入该系学习。军艺的学习对莫言的创作影响巨大,他曾说:“军艺使我的创作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1985年,莫言发表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赢得全国性声誉,这是他的成名作。这部小说与短篇小说《枯河》是姐妹篇,都有莫言少年时期当童工的惨痛记忆。 后来,他摸索着前进,走自己的路,成功了。 我感悟到: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硕士学位以至博士学位的,至今没见人问鼎文学诺奖,而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在社会的历练中自学成才的莫言,居然成为了诺奖获得者; 神州大地普通乡村万万千,齐鲁大地穷乡僻壤的东北乡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文学圣地。 这一切来的多么突然, 不可思议。可是我说,这里又蕴涵着许多必然。
|